浅析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界定
2019-12-30 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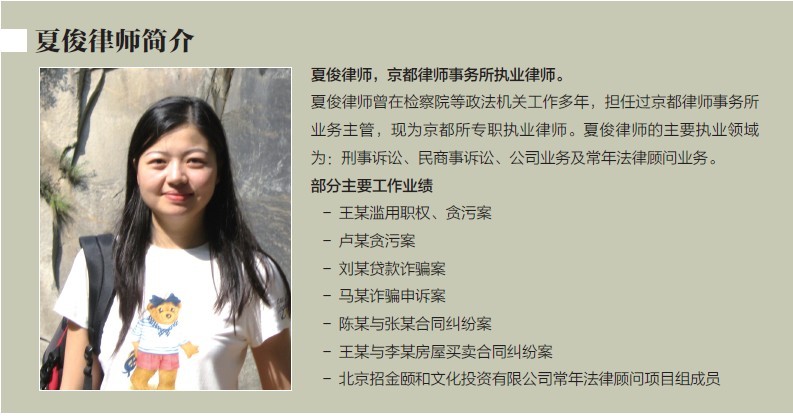
现行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寻衅滋事罪由旧刑法的“流氓罪”分解而来,其规定为:有 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 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 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其第一种情形,即“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作为常见多发罪名,如何区分“随意殴打型”的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尤其是造成轻伤害结果的案件中,此罪与彼罪的定性之争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难题。近年来发生的“方舟子遇袭案”、[1]武汉被拆迁户童贻鸿寻衅滋事案[2]等公共事件,均出现了寻衅滋事罪的身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传统观点将主观上的“流氓动机、无事生非”作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而与故意伤害罪相区别。但该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无从认定,导致个案分歧争议不断。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是寻衅滋事罪的本质特征,发生在公共场所是扰乱公共秩序前提条件,也是区别于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实践中,应以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寻衅滋事罪“口袋化”之趋向。
如何界定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笔者也做一粗浅的分析。
问题的提出及语境的限定
实践中的困惑与尴尬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衅”即嫌隙、争端,“寻衅”便是故意挑起事端;“滋事”即惹事、制造纠纷,寻衅滋事可以解释为故意惹事、制造纠纷。通说一般认为,寻衅滋事罪的特征在于“无事生非”,其认定的核心要素是主观上的流氓动机,即为逞威风、逗乐开心、寻求精神刺激而实施殴打他人等行为。这是其区别于相关的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等罪的关键。[3]还有观点将主观上的流氓动机进一步解释,分为“无端滋事型”和“小题大做型”,后者是指行为人殴打他人的原因不符合常理,强盗逻辑。[4]然而,上述理论看似清晰,在实践中却无法有效适用。
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寻衅滋事案例却与上述理论相悖。“无事生非”的寻衅案件在实践中越来越少。如2009年上海某区法院审结的88起寻衅滋事案,确为事出有因的占59.09%。[5]上海某区检察院公诉一处2010年度受理的164起寻衅滋事案件,除了17起为行为人酒后无端滋事外,其余约90%的寻衅滋事案均存在各种缘由,如两促销员因为在超市争夺顾客而引发的殴打、棋牌室内因为口角而引发的斗殴报复、KTV里因争风吃醋引起的殴打他人、小区里因为停车纠纷而引起的殴打、因债权债务纠纷而引发的打砸宾馆案等等,[6]均为事出有因的殴打行为。且仔细分析上述案件发生的缘由,虽然有些不理智与逞强的成分,但也并非“你在街上多看我一眼我就要打你”式的强盗逻辑。上述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公检法三家的定性均无二致,直至最后判决生效。由此看来,主观上的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罪认定要件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许会逐渐被摒弃。[7]
另一方面,因为定罪标准的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案件被“套”上了寻衅滋事罪的外衣。[8]之所以说“套”,是因为其事实本不符合 该罪构成,但在实践中出于各种理由,有关部门牵强附会地认定为该罪。如方舟子遇袭案,根据其案情陈述,很显然是故意伤害,但鉴于本案没有造成轻伤害以上的 结果,对于伤害未遂的处罚与否无法确定,为了将被告绳之于法以满足激愤的民意,办案部门于是打了个“寻衅滋事罪”的擦边球
可以预见,在维稳压力不断增大、追求“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背景下,这种“套用”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甚至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如此继续,罪刑法定原则构建的人权保障机制恐岌岌可危,以法治限制公权力恣意的良愿将愈发渺茫。以至于有论者发出了“别让寻衅滋事罪异化为整治公民的乖缪借口”的呼吁![9]
寻衅滋事罪客观存在背景下的探讨
鉴于寻衅滋事罪认定标准模糊,与相关罪名区别困难,而且有演化成新“口袋罪”的趋势,已经有不少论者提出质疑,或主张废除寻衅滋事罪,[10] 或者建议将寻衅滋事罪分解为其他相关罪名,[11]其实质与废止论无异。
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仍有存在的必要。本罪立法的初衷定位于“妨害社会公共秩序”范畴,不同于针对特定个 人的故意伤害等罪。实践中仍有不少严重危害社会、引起极大民愤的行为,如公然殴打他人、多次殴打、殴打老弱病残、公然破坏毁损公共财物等,造成公共秩序混 乱,侵害公民善良情感,但其行为往往未造成轻伤以上结果、数额到不到相关立案标准,无法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将其绳之以法,如废除本罪,将导致法 益保护的缺位。事实上,任何立法不可能尽善尽美,刑法罪名的设立也不例外。理论者的任务不是简单的拆除抛弃,而是以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精神作出合理解释,以 智慧弥补立法的不足,熨平立法的褶皱。正所谓“心中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作出公平正义的解释”。[12] 这才是更重要,当然也是更难能可贵的!
退一步讲,是否应该废除 本罪暂且不论,作为司法者,在立法未能改变、寻衅滋事罪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案件不断发生的现实条件下,所要做的是如何精准的理解立法者意图、如何更好的适 用本罪。另外,从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作出修正的情况来看,本罪不但没有被废除的迹象,而且还有长期存在的较大可能。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意图,笔者将以轻伤害结果的案件为切入,探讨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不同认定。
“流氓动机论”之反对
流氓动机论源于旧刑法制定时的“泛道德主义刑法观”,已经不适应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今社会,且其内容含糊不清,无法有效区分此罪与彼罪。
基于历史沿革解释得出的结论
历史解释是指,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述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意味着参考法条的来龙去脉等因素得出解释结论。[13]
“两高”1984年11月2日《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 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流氓罪行虽然往往使公民的人身或公私财产遭受损害,但其本质特征是公然藐视法纪,以凶残、下流的手段破坏社会秩 序,包括破坏公共场所和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修订刑法时,立法者以分解的形式在新刑法中实质上保留了流氓罪。寻衅滋事罪便是继承流氓罪衣钵的罪名之一。上 述司法解释依然影响了人们对新刑法中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于是多数教材通说将注释的视角集中于“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毁损公私财物”等字眼,将“流氓动机”作为认定本罪的主观要件。
“流氓动机论”不符合当今时代背景
寻衅滋事罪来源于旧刑法的“流氓罪”,因此考察本罪不得不回到其源头。“流氓”一词最初是指从外地流入上海无工作的盲流,后来演化成无所事事、惹是生非、没事找事、调戏妇女、恣意殴打他人或强拿硬要财物等混迹于公共场所,寻求精神刺激、发泄不满、逞强斗狠等心理不健康的一群特殊群体,对社会公共秩序具有严重破坏性,因而纳入旧刑法惩罚范围。[14] 众所周知,旧刑法诞生于1978年前后,彼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革时期对法治批判的余孽尚未散去,我国虽历尽艰辛,制定刑法典,但其罪名设置的粗糙和认定标准的模糊成为共性。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经历了三次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严打运动”,流氓罪在严打过程中成为最常见的罪名之一。在那个“泛道德主义”刑法观主导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年代,流氓罪极大地满足了当权者“治乱世用重典”的需求,对于一般打架斗殴、男女关系不检点等均纳入流氓罪予以惩治,很好的扩大了刑罚的打击面,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刑罚的威慑作用,因而该罪一直为立法者所偏爱。
而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不得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迅速发展的同时是民众道德观念的更新、价值观的多元化。一方面,人们对所谓的“流氓行为”愈发宽容,道德归道德,刑法归刑法,严打时代所憎恶的“流氓行为”,如今看来不过是个人生 活方式选择的一种,抑或只是道德评价范围,很难再上升为犯罪高度。一方面,如今社会所认为的流氓行为越来越少,能够上升为犯罪行为的流氓行为更是为数不 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追求经济利益成为人与人交往的重要目的,寻衅滋事式的打架斗殴往往直接或间接出于经济利益的纠葛,或者出于其他争端,诸如争风 吃醋、报复陷害等等。纯粹寻求精神刺激或填补精神空虚式的寻衅滋事,在当下越来越少。
因此,将所谓“流氓动机”、“追求精神刺激”作为寻衅滋事罪主观特征的观点,已经不符合时代背景,值得商榷。
“流氓动机”的认定标准模糊不清
对于何为“流氓动机”、“随意殴打”,各方论者可谓殚精竭虑,尝试着从各种角度作出解释,试图提出一种可行的鉴别方法。如有论者提出的“双重置换法”:将殴打的行为人置换成他人,则他人不会实施殴打行为;将被殴打的人置换为他人,则行为人仍会实施殴打。如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认定为“随意殴打”,构成寻衅滋事罪。[15] 但其实质仍为主观动机是否合理,如果严格按照双重置换规则,实践中几乎没有寻衅滋事罪可言。前文已述,如今以殴打别人取乐、在街上随便找个不认识的人就打的情形已经十分少见,同时符合该置换规则的几乎不存在。换言之,无事生非型的寻衅滋事在实践中越来越少。
另外,“小题大做型”的寻衅滋事也存在争议。也即殴打他人虽有理由,但该理由明显违背常理,不符合一般人的标准。但何谓“相对合理的理由”?何谓“一般人的标准”?这些在实践中也难以统 一掌握。如案例一:被告人甲因在棋牌室与人发生口角,便于次日指使其朋友乙丙等人,一同至棋牌室殴打被害人丁,致丁轻伤。本案检方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后得 法院支持判决。案例二:被告人张某因购买热水袋质量问题,与店主李某发生口角,张某便伙同其姐夫王某前去找店主算账,后二人持刀将店主李某及前来劝架的李 某之妻砍伤,经鉴定为一轻伤、一轻微伤。本案检方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后法院也以同罪判决。以上两案,一是出于口角而报复殴打,一是出于买卖纠纷而动手殴打 他人,何者为合理?何者为不合理?众说纷纭,更多的是依靠办案人员的个人智慧和社会经验,如此认定,难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现行刑法之下,主观上的流氓动机不应成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客观场所说”之提倡
相比于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更直观、明晰,认定犯罪应以客观要素为基础。客观主义刑法理论,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理念、有利于合理区分刑法与道德、有利于合理对待犯罪化与非罪化。评价寻衅滋事的罪与非罪,应首先着眼于客观要素。
寻衅滋事罪的本质是妨害社会公共秩序
寻衅滋事规定于分则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并在其罪状中明文规定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才成立本罪。因此其侵害的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这是本罪区别于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等罪的关键。
“社会公共秩序”也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以及由此上升的社会稳定有序状态。社会公共秩序的法益离不开具体的个人,就“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而言,其侵害的是“社会一般交往中的个人身体安全,或者说是与公共秩序相关联的个人身体安全”。[16] 这正是寻衅滋事罪的本质特征。正因为如此,行为人随意殴打家庭成员,或者基于特殊原因殴打特定个人,或者在隐秘场所殴打被害人的,没有涉及侵害公共秩序的,不可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发生在公共场所是侵害公共秩序法益的前提
侵害公共秩序法益的前提 是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所谓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的人可以自由进出或履行相关手续之后自由进出的场所,如车站、影院、马路等地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当暴力分子在公共场所对某一个体进行殴打时,公众在对被殴打者怜悯同时也会顾影自怜,当这一情绪反射于大脑,公众就会降低对公共场所安全的信任 度,因而这并非是简单个体之间的私人恩怨或彼此伤害,而是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扰乱和破坏。[17] 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殴打等行为,才有为不特定民众所感知,进而上升为都社会秩序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才可能侵害社会公共秩序。
参照国务院颁布2006年3月1日起实施的《公共场所管 理条例》,公共场所包括:(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三)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六)商场(店)、书店;(七)候诊室、 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场所还必须考虑其实质上是否存在“妨害社会公共秩序”的可能。从时间上看,不少公共场所有营业时间的限制,非营业时间不能认定为公共场所,如关门的网吧、停止使用的候机室等。另外,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不特定人在活动,唯有如此,寻衅滋事行为才能对社会成员造成恐惧等心理压力。[18]
以公共场所为核心区别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
发生在公共场所只是认定 寻衅滋事罪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也即并非所有的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殴打行为均可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司法实践中,以发生的场所来定位侵害的法益,再参 考行为人供述所反映的主观动机、客观上的行为方式、行为对象等因素,进而综合认定寻衅滋事罪成立,是最有效的判断方式。
1.发生在公共场所以外的殴打行为不定寻衅滋事罪
公共场所是认定妨害社会 公共秩序的前提。因此,如果发生在公共场所以外的殴打行为,则不涉及公共秩序法益的侵害与否,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如果造成轻伤以上结果的,应以故意伤 害罪论处。典型的非公共场所如,个人家中、单位办公室内、宾馆房间等场所;另外一些常见的公共场所,在特殊的时间、背景下,不具备妨害社会公共秩序可能 的,也不涉及公共秩序的妨害。如深夜僻静的街头巷尾、已经关门停业的网吧、停运的公共交通
工具等。
2.发生在公共场所以内的殴打行为一般定寻衅滋事罪
发生在公共场所内的殴打 行为,如果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但情节恶劣,如多次殴打他人、殴打老弱病残、引起社会公共秩序混乱等,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如果造成轻伤的后果,可以视为 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故意伤害罪轻伤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寻衅滋事罪是五年以下,相较而言后者更重,所以应定寻衅滋事 罪。
3.造成重伤及以上结果的应定故意伤害罪
一般认为,殴打他人造成重伤及以上结果的,应定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法定最高刑是五年(尽管刑法修正案八将寻衅滋事罪最高刑提高到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但其仅针对“纠集他人多次实施”的情形而言,无法涵盖较常见的致被害人重伤的情形),其法定刑不能包容重伤以上的结果,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定故意伤害罪为宜。
注释:
[1] 2010年8月29日,方舟子在家门口附近被人用辣椒水袭击面部、锤子砸伤腰部,致其腰部皮肤挫伤。警方事后查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肖传国花十万元雇佣他人实施上述行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肖传国拘役五个月,二审维持。参见未名:《方舟子遇歹徒袭击》专题报道,载http://news.163.com/special/fangzhouziyuxi/,2011年3月19日访问,另外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及各大新闻媒体均有报道。
[2] 2010年11月18日,武汉被拆迁户童贻鸿向强拆人员扔石块,后警方称其“导致一人重伤”通知其前去做笔录。童因不信任当地警方,而坐飞机前往北京朝阳某派出所自首,后被移送武汉警方,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后检方以故意伤害罪将其批准逮捕。此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参见杨杰:《武汉钉子户不信任当地警方乘飞机赴京自首》,载http://news.sina.com.cn/c/2010-11-21/023021506346.shtml,2011年3月19日访问。
[3]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务实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0-1281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页;《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学》第二版(2003年版)中也持上述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之后修订了上述观点,认为“在现行刑法之下,没有也不应当将流氓动机作为本罪的主观构成要素”,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68页。
[4] 王金贵:《如何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6期(上)。
[5] 潘庸鲁:《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比较》,载《法治论丛》2011年第1期。
[6] 上述资料由相关检察院办案系统收集整理而来。
[7] 当然由于资料限制,笔者掌握的实践案例代表性有限,无法充分论证该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有理论在实践中适用出现较大争议。如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分歧,表现为刑拘转逮捕比例较低,参见史杜军:《论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的认定》,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也有法官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也较大质疑,参见梁剑 叶良芳:《寻衅滋事罪立法规定质疑》,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6期;潘庸鲁:《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比较》,载《法治论丛》2011年第1期。
[8] 影响较大的还有“赵连海寻衅滋事案”,赵原系媒体记者,因其儿子服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肾结石,其被指控利用三聚氰胺和其他事件,纠集群众和境外媒体记者到公安局外聚集扰乱社会秩序,后被北京石景山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参见《南方都市报》:《“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获刑两年半》,载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101111/ArticelA25006FM.htm,2011年3月19日访问。
[9] 张若渔:《别让寻衅滋事罪异化为整治公民的乖缪借口》,载http://hlj.rednet.cn/c/2010/11/22/2118462.htm,2011年3月19日访问。
[10] 王良顺《寻衅滋事罪废止论》,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11] 周军《将寻衅滋事罪分解的可行性探究》,载《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2] 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原理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3] 张明楷著:《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14] 潘庸鲁:《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比较》,载《法治论丛》2011年第1期。
[15] 何庆仁:《寻衅滋事罪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4期。
[16] 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载《法律与政治》2008年第1期。
[17] 潘庸鲁:《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比较》,载《法治论丛》2011年第1期。
[18] 王金贵:《如何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6期(上)。